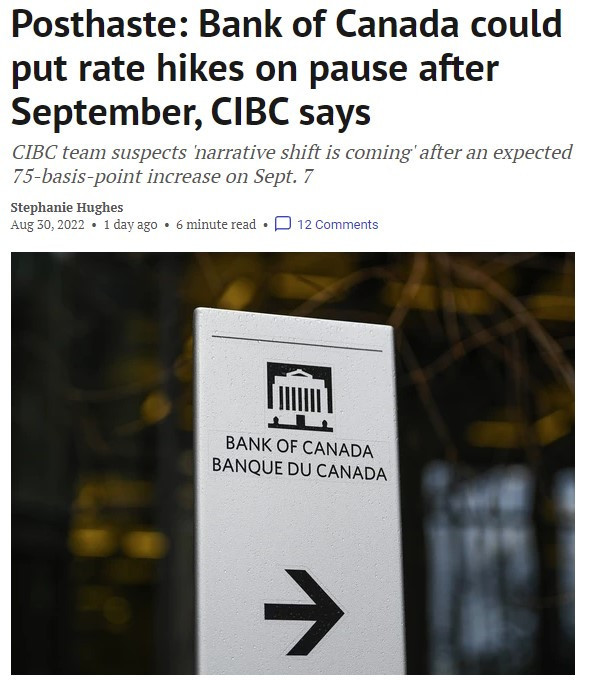网传中国着名法学家、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抓,在北京家中被十多名警察带走。。
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许章润朋友确认消息,四川警方通知许章润家人,指他在成都嫖娼,不过据其友人表示,许章润一直留在北京。
微博搜索许章润已被清除。
知名学者,1962年生于安徽庐江县。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华人法哲学协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宪政、儒家人文主义的法律义理等。主持《历史法学》集刊,主编《汉语法学文丛》。著有《说法·活法·立法》、《法学家的智慧》、《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以及散文集《六事集》、《坐待天明》等,2014年12月出版《汉语法学论纲》。
沪上研讨,是为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而召开,许章润作为法学界唯一的代表参会。“1915年开始新文化运动,我们法学界1902年就已开始,且直接跳过思想启蒙阶段,把西方的制度果实拿来作为中国法制的起点。所以,不妨说,法学界走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头。”会议现场,许章润调侃道。不过,事实证明,没有思想启蒙,即便制度已经嫁接,亦得不到落实。
许章润认为,这一波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已到收尾阶段,“某种意义上,启蒙进行得差不多了,主流价值观念早已发生极大变化”,时至今日,需要借此“实现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肉身化”。
肩负中国法学本土化使命
2003年,在数场演讲中,许章润提出“汉语法学”的概念,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语法学”的短文。积十年之功,2014年12月,《汉语法学论纲》出版面世。在许章润看来,时代流变并没有影响研究方向,反而提供了现实佐证。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现在,中国法律人越来越意识到,晚近接引的法学理论若要落地生根,必须本土化。”许章润认为,这十多年,法律人的理论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而在理论层面来加以总结、阐述——许章润称之为“时代使命”,他乐于肩负。
“在其他媒体的采访中,我看你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记者问。
“是啊,总得做事。”许章润说。担负这一使命,需要深入研究英美法学、大陆法学等,进而反观中国法学,且要了解世界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另外要对中国的古典文明包括儒学有所钻研。三者叠加,他觉得这些条件自己“庶几乎具备”——“我不是最佳人选,但挺合适”。
这种豪情只是偶尔流露。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办公室墙上,一幅朋友送来的书法写着“汉语法学之父”,后面两个字,许章润用书桌遮掩了起来。
并非要与西方法学接轨
今年1月30日,“2014十大法治图书”评选出炉,《汉语法学论纲》位列榜首。至于这本书,获奖图书评委会认为,对汉语法学的梳理,是迈往“法学世界杯”的第一步,并写道:“他(指许章润)在深入挖掘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明背后的价值思想脉络,并寻找其与现代法学的转轨对接途径……”
“跟哪个现代法学接轨啊?”采访时,许章润疑惑起来。他觉得,这一说法“牛头不对马嘴”,“至少我没有这个用意”——“汉语法学本身就是现代法学,是现代中国的法律文明,所以不存在跟谁接轨的问题。”
转轨对接的说法,反映出中国法学界的西方中心视角,但实际上,之所以写作《汉语法学论纲》,许章润正希望打破“西方中心视角”,解决中国法学本土化的问题。发表获奖感言时,他坦言此书并非应对西方挑战的“激烈之作”。新书开篇,他同样强调,“秉持中国身份和中国文明立场”,立足当下,“发掘理述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
■ 对话许章润
谈“法学世界杯”
穿自己的球衣,打不打得赢,先上场
新京报:在“2014十大法治图书”榜单上,你的新书上榜,有人评介时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法学世界杯”。
许章润:对。这是在世界法学格局中立论,除了汉语法学,晚近以还,世界法学家族中主要包括英语法学、德语法学、法语法学、西班牙语法学、阿拉伯语法学。俄罗斯比较悲催,斯拉夫系统原来自成体系,但是后来分崩离析,除了俄罗斯之外,在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影响,此前的加盟共和国纷纷采用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
在世界法律文明的大格局中,我们十三亿中国人的法律精神世界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主体性?从这个角度讲,“法学世界杯”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词,为什么?各自发展,服务自家的生活世界,谈不上竞争或较量。
新京报:但这个词也侧面表达了一个事实:“汉语法学”给人的印象是处于弱势。
许章润:确实是这样。因为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模仿、引入,现在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但是没有自己的东西,所以有欧美人说,你们的法学不过是我们的一个分支而已。
新京报:按照“法学世界杯”的说法,在你看来,汉语法学“入场”了吗?
许章润:早已入场,用自己的球员,但是,穿着别人的球衣。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蔡枢衡就讲过,中国没有自己的法学,在中国只有西方法学——他很痛恨这一点。但是,与此同时,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中国人开始着手探索,杨鸿烈、陈顾远等都在理述中华法系,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表述。到我们这个时候,开始明确表述——用自己的球员,穿自己的球衣,打不打得赢,先上场。
过去我们一直穿着别人的球衣,反映在教科书上,比如讲到“法律行为”,都是写英美法系是怎么认为的,大陆法系是怎么认为的,日本是怎么认为的,甚至说到台湾学者,最后才说到自己的看法。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怎么学习、消化别人的东西,其实并没有自己的主体理论。
当然,另一方面,法律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一旦某一方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一个向全球传播的问题。过去中华法系,传播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成为了这些国家自己的东西,那么,现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传播到东亚,从源头来说,这是别人的,但是如果扎下根的话,就是我们的——至于如何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勾连起来,和我们血脉相连,那就得费一番工夫——汉语法学的功夫。
新京报:你写作、出版《汉语法学论纲》,从法学的角度来说,面对的时代环境是怎样的?
许章润:这就是问题意识。促使我研究的问题意识,乃是这样一种时代语境:1902年,满清末年中国开始变法,在制度层面引入了西式的规则,但是义理层面的融合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未曾完全成功过。这期间有两脉线索,一脉是所谓“礼教派”,主张必须用中国的义理来面对西方的规则,但是中国的法意和西方规则有时候是难以融合的;还有一脉是所谓“新派”或者“法理派”,多少主张全盘接纳。新文化运动1915年开始,但其实,中国法学的中西融合工作,1902年就已经开始。后来的发展,“新派”占了上风——“新派”也分两脉,一脉是1949年以前以欧美为模仿对象,一脉是1949年以后以苏俄为模仿对象,1978年以后又重新模仿欧美。
百年的发展,应该说有利有弊,其中一弊是丧失了用自家的语言来表达中国问题的敏感性,一旦这种敏感性丧失,也就丧失了对于问题的真切的把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汉语法学,实质上是要从语词层面渗入到规范的义理层面——因为任何规范,总是要通过词句来表达,而词句是存在的家园,也就是规范的实在形式。
还有一点,从1902年到现在,这一百一十多年的时间,大规模移植西法的阶段基本上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整体性整合,而整合是要从规范、义理、语词和实践这几个方面同时着手。我讲汉语法学,是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背景,以中国一百多年的法制建设为基本素材,在这个基础上将中国这一“古今中西”时代所激荡产生的法制与法意重新加以整合,缔造出一种新型的基于中国文明脉络的法制与法意。
新京报:接下来呢?
许章润:规范、义理、语词的整合,只是汉语法学的第一层面。第二层面,是分析、提炼出中国人的法律智慧,比如我在书中讲到历史主义意识、基于人性本恶但憧憬人性善好的“心性论”、“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这些都是我们一直不讲的,或者曾经作为文化糟粕大加挞伐的,或者没有总结出来但是现在需要讲出来加以总结的。第三层面,由此进入到知识理论层面的创发性作业。西方有历史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中国有什么呢?需要梳理出来。第四层面,指向规则层面,这些理念、法意、义理结构等是如何影响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这四者,缺一不可。这本书进入了四个层面,但更多的是在阐述、总结前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不是一本书所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新京报:但第四层面,好像正是人们最关切的问题?
许章润:从我这个思路,大家关心的,是为什么有法不依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恰恰是这些现实问题的追问,反馈回法理层面,要求法律作出解释,而解释需要拓宽思路,其中思路之一就是“汉语法学”,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乃至于秦汉以来两千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法律义理结构之中,找出蛛丝马迹,以获得思想资源,回应当下法治的现实困境。但是,这件事不能急功近利。 (记者 吴亚顺)
来源: 半月谈网
 新华侨网
新华侨网